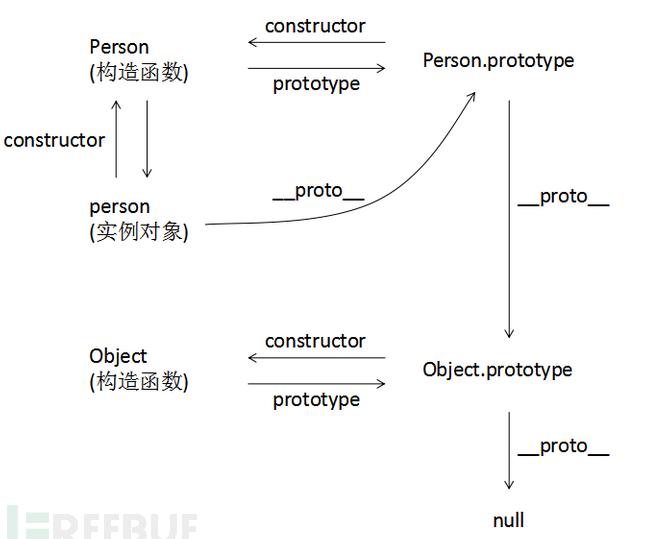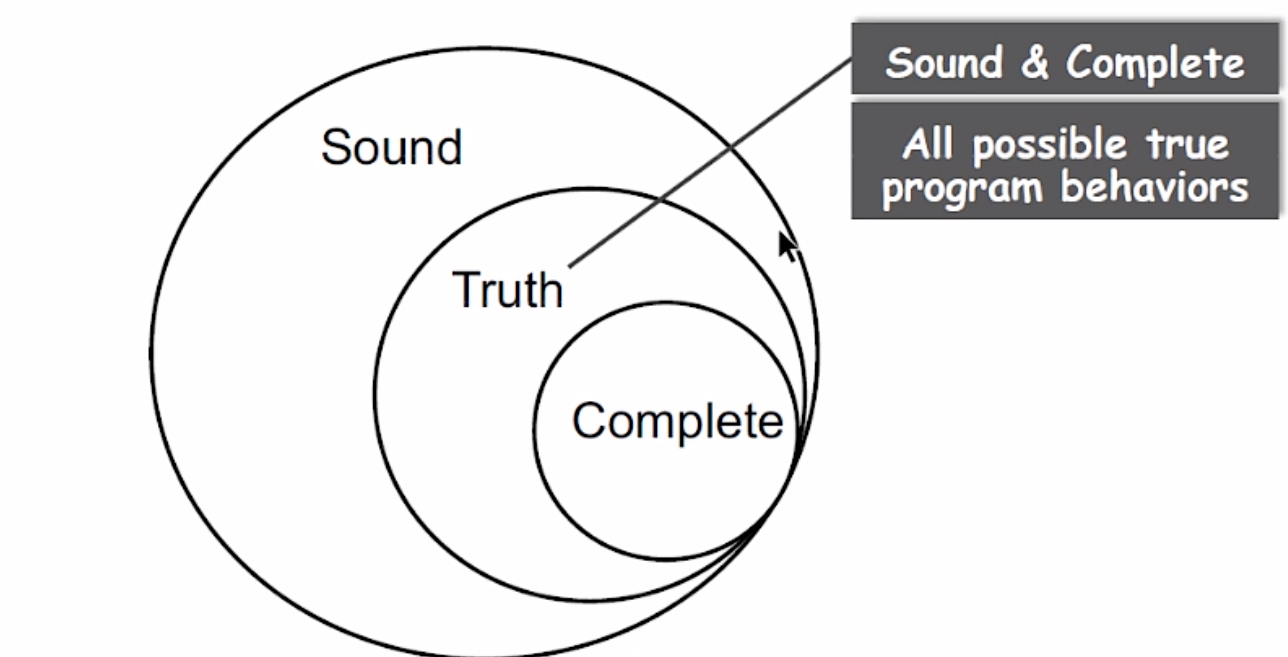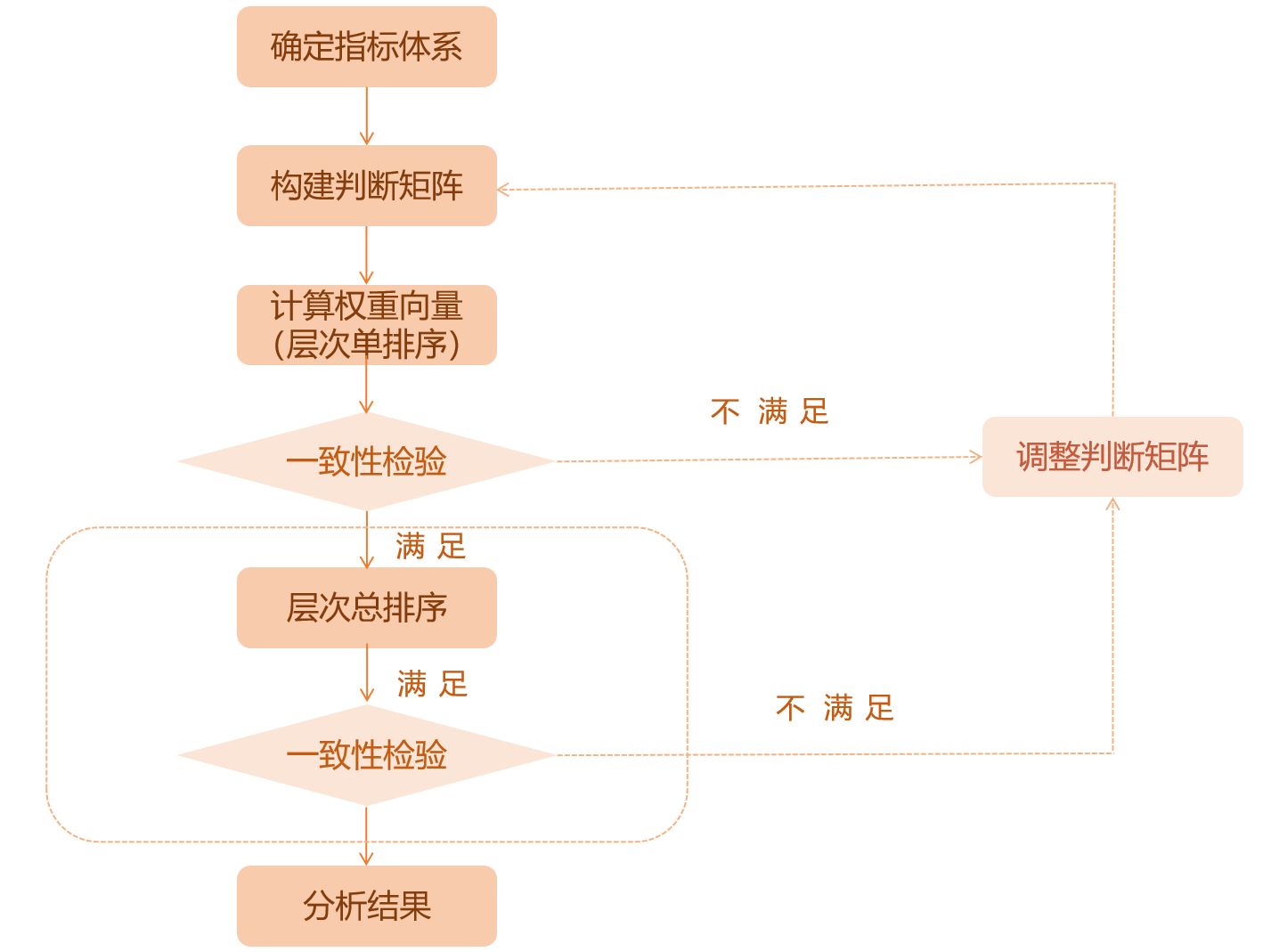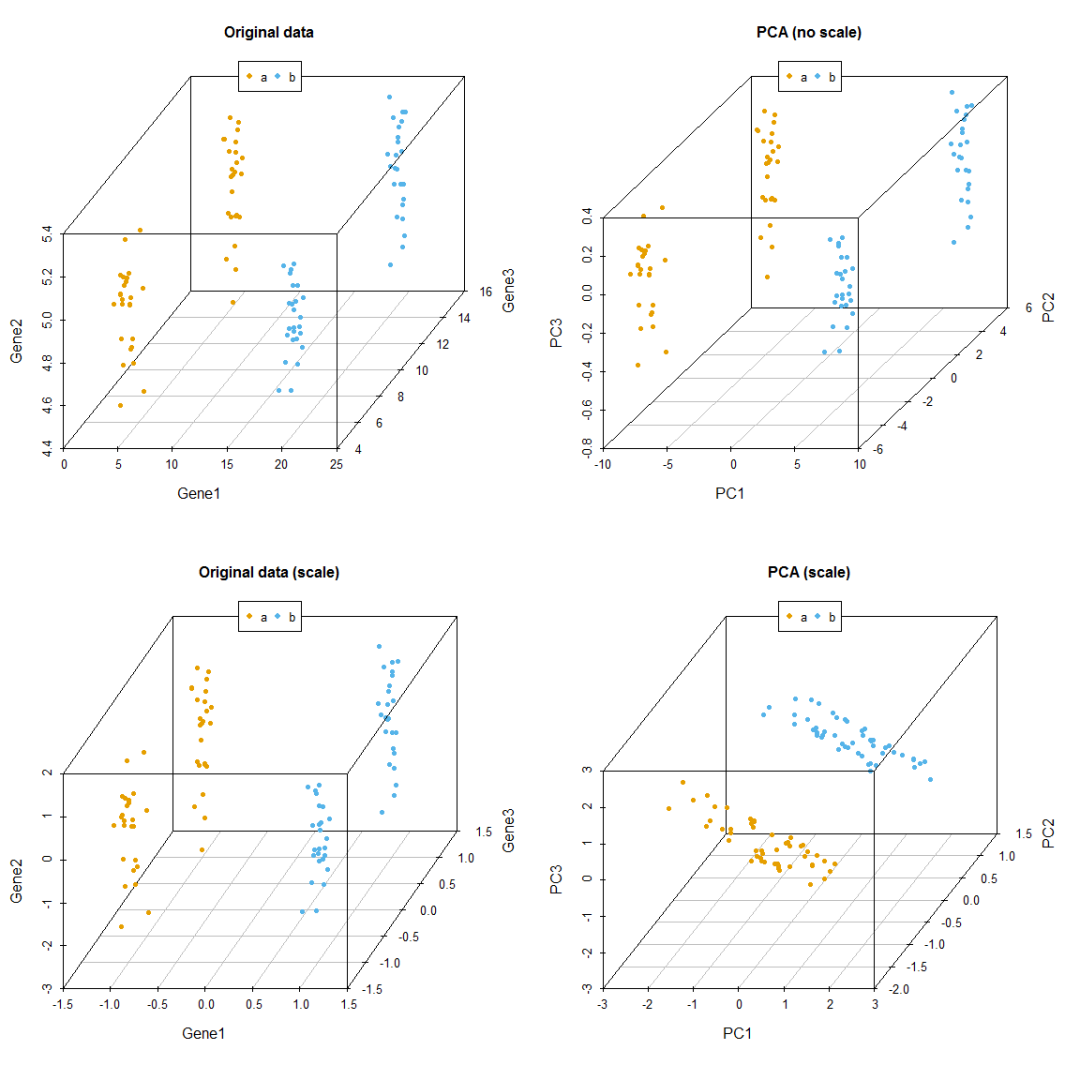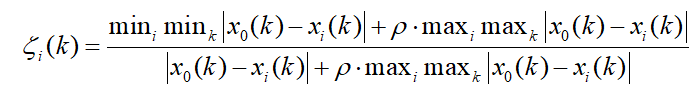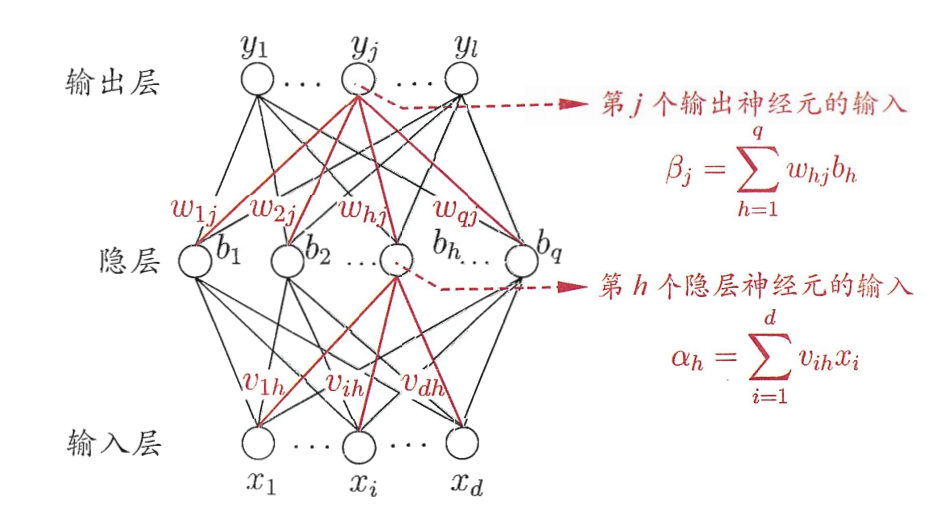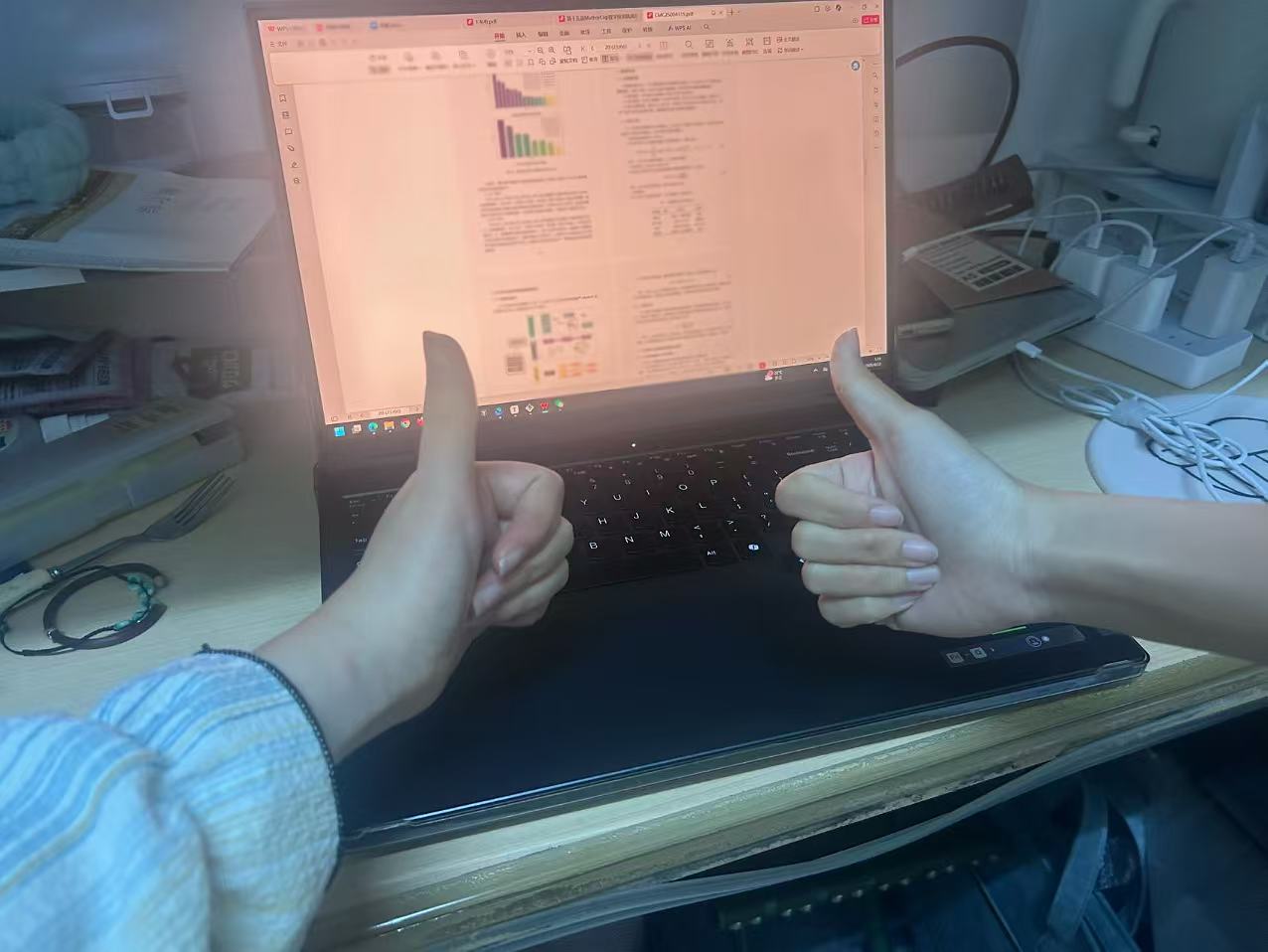《归藏》者,藏之归也。
影
会场灯光明亮,水晶吊灯在头顶闪烁,映出一张张凝神屏息的脸。红木讲台后,拍卖师身着剪裁得体的西装,手持拍槌,语速飞快地介绍着下一件藏品。台下座无虚席,竞拍者们或举着号牌,或低声交流,神情紧张而期待。
终于,到了本次拍卖会的重头戏。
陆怀远缓缓抬头,指尖摩挲着苏富比拍卖目录,封面上那尊羊首铜像的浮雕轮廓被灯光映得忽明忽暗。他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参加这样的拍卖了,但这一场,却格外沉重。他的目光落在展台中央,白布揭开的一刻,全场顿时安静。铜光闪烁,羊首端庄肃穆,眼眸中似含未尽之泪,仿佛穿越百年硝烟重现于世。
拍卖师微微一笑,抬手挥过展台:“本场重器,清乾隆时期羊首铜像一尊,起拍价——五十万英镑。”
他声音一落,角落里霍华德伯爵靠着拐杖缓缓站起。他身形颀长,神态悠闲,身后站着的年轻代理人举起号牌:“六十万。”
“七十万。”有东南亚口音的买家也随即出价。
陆怀远一顿,彷佛在思忖着什么。
一旁,陆明昭坐得不甚耐烦,低头刷着手机,时不时瞥父亲一眼,眼神里藏着焦急。他低声说道:“爸,再犹豫就来不及了。您不是说这东西意义重大吗?”
陆怀远皱起眉,眼神开始变得复杂。他的思绪忽然被一缕雪茄烟香牵走,转头看见霍华德伯爵正在慢悠悠地吐烟,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。那神情,令他猛然回忆起1993年香港佳士得秋拍——那年,一尊西周青铜鼎被日本商人拍走。
“爸。”陆明昭又轻唤了一声。
“八十万。”陆怀远举起号牌,他的声音有些低沉,仿佛是在对自己交代。霍华德微微一笑,尚未开口,他的代理人已然不动声色地举牌:“一百五十万。”
“二百万!”现场爆出一阵轻微惊呼,节奏陡然紧张。陆怀远的眼皮一跳,忍不住握紧手中的银杏木号牌。他手上的和田玉扳指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,是他恩师临终时留下的旧物,扳指上的螭龙纹,被他指腹来回摩挲。
“爸,不能停。”陆明昭声音低而坚定,“这不只是拍卖,是立场。”
“陆先生该不会连三百万都拿不出吧?”霍华德掀开怀表盖,轻轻晃了晃,链子末端吊着一枚纪念金章,熠熠生辉,“这可比他们当年从圆明园运回伦敦的费用都低。”
话锋冷嘲又含威慑。
拍卖价已飙至三百二十万,仍未见尽头。陆怀远手微颤,再次举牌。
“三百五十万。”拍卖师毫不迟疑地重复,现场鸦雀无声。
“爸!”陆明昭的嗓音提高了些,“别再犹豫了!我们不是来观望的。”
陆怀远却没有再举牌。他眼神凝重,望向那尊铜像。他退回座位,身子靠进椅背,一言不发。
“陆先生,不再继续出价吗?”拍卖师彬彬有礼地看着他,全场目光聚焦。
他摇了摇头。
陆明昭惊愕地望着父亲:“你放弃了?”
没有回答。
“你说过文物无价,你说过要把它带回国——可你现在在干什么?”他的声音压低,但满是失望与怒气,“你根本不想拿它回来,对吧?你怕了?不愿意拿这么多钱出来是吧?就守着你那破公司吧”
陆怀远转头望着儿子,眼里掠过一抹难以言说的情绪,终究没说出一句解释。
陆明昭站起身,拿起西装外套大步离去。那背影,像极了二十年前的自己——年轻、愤怒、不顾一切。
拍卖会还在继续。铜槌落下的一刻,霍华德伯爵轻轻点头,脸上依旧挂着那抹不动声色的笑意。他抬手接过代理人递来的香槟,轻轻一碰杯,仿佛为这场戏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陆怀远依旧坐着,目光落在台上那尊羊首铜像上,眼神深沉而幽远。他的手指仍在摩挲玉扳指,像是在抚摸一段早已尘封的过往。
潜
伦敦午夜,得令人窒息。厚重的夜幕压在宫墙之上,一只红外摄像头在微微摇头,而它所捕捉的画面中,一抹黑影正沿着雨水管滑入地宫深处。
陆明昭的夜视镜闪过幽红,视野里通风管道锈蚀斑斑。老鼠从一张残破古卷上跃过。没人知道,这页佛经残章,是某位英籍勋爵从敦煌莫高窟私运出来的真迹,如今却躺在金库废气口下,任鼠牙啃噬。
“真是浪费。”陆明昭咬牙,手指快速调整着登山绳的速降器。脚下的防弹玻璃展柜泛着森冷光泽。
他蹲下,输入提前偷录下的指纹模板,锁“咔哒”一声解开。
展柜开启的瞬间,那是沉睡在百年岁月中的气息,是火与水共同浸泡的气味,是圆明园大火后遗物烧焦却未灭的余温。
铜羊首静静伫立,眼窝内嵌黑曜石,凝视着半空中的什么。他伸手欲取,一道红外线网格骤然亮起,墙面宛如蛛网闪出警戒线条。
警报声刺破静夜。
地宫铁门猛地开启,两个穿制服的保安将陆明昭摁倒在地,他被死死按在编号“1840”的铁箱上。他挣扎,却抬眼一看——霍华德伯爵正缓缓踱步而来,身后拖着披着天鹅绒的推车,拐杖在石地板上敲出不紧不慢的节奏。
“年轻人真有意思。”霍华德微笑着,俯下身看向陆明昭,“你父亲知道吗?”
“你根本不配拥有它。”陆明昭怒吼。
伯爵耸耸肩,转头看向那只羊首:“我?我当然不配。但它现在是我的,你抢不走。放在金库一角,没人欣赏,也没人打理。你看这潮湿的空气、闭塞的空间,那些东方的神灵和信仰,不就是这样慢慢腐蚀掉的吗?”
“你知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?”
“当然。”霍华德冷笑,“它意味着——在你们一部分人眼里,这玩意儿是祖国的伤疤,是民族的情感勒索。而我,只是想从中赚一笔爱国税而已。”
这时,一道浑厚的声音从门口传来:
“你这一笔,赚不到了。”
陆怀远缓步走入金库,目光从羊首掠过,最终落在儿子的脸上。
霍华德摊开手,嘲讽地一笑:“你不在拍卖会上出手,很令我惊讶啊。你的民族情怀呢,你的大义呢?这不是你们黄种人最重视得吗?”
陆怀远没有理他,只是走到展柜边。羊首静静伫立,铜胎上微弱的光芒像是来自另一个朝代的注视。半响,他盯着霍华德看着,微怒。
“我说了,我不在乎这玩意儿。”霍华德耸肩,“你们在乎罢了。”
“我们在乎。”陆明昭忽然开口,“你不配碰它。”
“可惜你父亲连碰它的勇气都没有。”伯爵嘴角一弯,“所以现在它还是我的。”
陆怀远轻轻转头,眼神在黑夜中异常清澈:“不,它不是。”
“文物的归属从不随着买卖而流动。你们抢走的不过是躯壳,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记忆,你们永远无法抢走,也永远无法抹去。‘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’,你们抢走了什么自己都不知道。但我们会永远记得。”
“顺便提一句,这笔买卖没成,你的上家好像不太满意呢。”
霍华德噤声。
陆怀远紧了紧前襟,拍了拍儿子的肩:“我们走。”
“就这么走?”霍华德冷笑,“不打算抢走它?”
“抢?我们还是不要同流合污了。”陆怀远淡淡道,“其实只要我们记得自己得来时路,记得那些过去,它还与不还都不那么重要了。”
陆明昭望着父亲,目光复杂。他想说些什么,嘴唇却微微颤动。
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,霍华德忽然笑道:
“喂,陆先生——”他挥挥手,“既然没能从你这敲出钱,那这铜像……送你了。”
陆怀远站住,回头望向他。
“就当是我承认错误吧。”霍华德戏谑地笑着,“反正它对我而言,只是一块破铜,留久了更卖不掉了。”
说完,他示意保安打开玻璃罩,将羊首铜像连同底座交到陆怀远手中。
那一刻,地宫沉默。仿佛连地下管道中的水滴声都凝固了。
陆明昭望着父亲细心捧起的动作,忽然意识到,这一块铜,不仅是流失的国宝,也是一段代际传承中,被沉默和误解压抑太久的信仰。
归
船离伦敦港已有六小时,甲板上风声猎猎,低沉如海兽的呼吸。凌晨四点,天色尚未泛白,甲板尽头孤零零立着一张金属桌,桌上覆着深灰色绒布,放着专业的玻璃盒,羊首安静地伫立其中。
陆明昭倚着栏杆,脚边搁着一瓶没开封的可乐。他已经盯着铜像看了半小时,却始终没有开口。
父亲陆怀远走来,在他身边坐下,取下手套,用酒精棉仔细擦去盒子表面附着的盐霜。
陆明昭终于没忍住,低声说,“我……突然觉得我们赢得不光彩。”
“怎么说?”
“我们没抢,也没买,是他扔给我们的——像扔给乞丐一块吃剩的骨头。”
陆怀远沉默了一会儿,将手中的棉球扔进密封袋:“我年轻时,也这么想过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我明白,真正尊严不是靠抢,也不是靠恨。”他顿了顿,“是靠你自己活得比他强。”
陆怀远望着远方黑海一线,“文物不是战利品,也不该是被人用来吊我们情绪的诱饵。外国人不在乎它——但他知道我们在乎。他拿着这东西当鱼钩,钓的不仅仅是钱,是情绪,是失控。”
陆明昭低头“我懂了”,又自嘲地笑了笑说“我那晚真的想抢走它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陆怀远看他一眼,“但你没抢成。”
“你知道我失败还去接我?”
“我怕你真抢成了。”
两人都笑了。
船舱内传来低低的引擎声,一只信鸽从桅杆上振翅而起,掠过黑暗天幕。片刻后,陆明昭突然问:“爸,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东西?”
陆怀远没立刻回答。他缓缓站起身,走到桌前,轻轻按住羊首底座。
“你知道这铜胎里为什么有裂纹吗?”
“火烤?”
“不是,是水。大火烧圆明园时,有人用井水往文物上泼,想救下一点,就这一点。”他说,“但水和火一起,铜就碎了。”
“那……还救吗?”
“当然救。因为再碎,它也是我们的历史。”
陆明昭静了许久。
“所以我们不是要让他们赔,而是要让自己配。”他像是自言自语,“配得起拥有它。”
陆怀远点了点头。
“我们要追索文物,不是为了复仇,而是为了修复历史地伤痕。”
“可那历史那么痛。”
“是。”陆怀远望着渐亮的东方天色,“所以才值得被铭记。你不记住它,别人就会重新改写它。”
船身微微一震,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海平面缓缓升起,照在铜羊首的面孔上。那张古老的兽面仿佛重新苏醒,在沉默中吐出被压抑百年的低语。
“爸。”陆明昭说,“我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了。”
父子相视一笑,鱼肚白泛起地红光愈演愈烈。
“准备好了?”陆怀远笑。
陆明昭望着远方升起的朝阳,深吸一口气。
“我准备好了。”他说。
风在身后掀起桌布一角,铜羊首依旧伫立,黑曜石的眼中第一次倒映出东方光芒。
铭
十年后,初春的北京,风从永定河畔穿过,一如记忆中圆明园断墙残垣间吹过的寒意。
陆明昭站在实验室的白光下,摘下护目镜。他的眼角已有淡淡的细纹,神情却比十年前更加沉静。他面前的,是一尊刚刚完成表面钝化处理的宋代铜佛像,断裂的指节已由他团队使用高精度3D扫描重建,并以离子束刻蚀还原了流失的纹理。
“陆老师,这尊佛像的刻字残损区找到了隐约的‘乾道元年’字样,我们是否要重建年款?”
身后的学生低声问。
他没有立刻回答,只伸手调出激光扫描仪的图谱,放大图像。在微米级纹理中,那几个字确实模糊得几近消失,却又未完全抹去。
“这不是为了让它完美。”他说,“是为了让它留下时间走过的痕迹。”
学生点头记下,转身离去。
他看着那佛像的眼睛,像是看见了十年前苏富比拍卖厅中,那尊铜羊首流转着沉默的光。他知道,那些文物真正的归属,不在某次出价成功的手中,而在千百次显微镜下的细致观察、在一次次数字还原与保护中的坚持。
手机振动轻响。
屏幕上,一封来自伦敦的电子邮件悄然跳出,抬头依旧熟悉:“Sotheby’s Private Invitation”。
他没有点开附件,只盯着那个信头发了会儿呆。那是十年来第一次,他们再度邀请他参与“东亚古物特别场”的拍卖会。
他忽然想起父亲。
那个拍卖会上没有出手的身影,那个背影孤独却坚定地转身离去的人——当年他以为那是退缩,如今才懂得那其实是节制,是某种分辨真正重要之物的能力。
陆明昭翻开父亲的工作笔记,泛黄的宣纸上洇着句未写完的题跋:”文物归处终有时,山河重光在…” 一滴浓墨从钢笔尖坠落,在”在”字后面晕开个永不凝固的墨晕。
风吹过窗棂,实验台上的铜锈粉微微扬起,在光里像极了那些曾被带走、又悄然归来的尘埃。
陆明昭拿起手机,又放下。他没有回复那封邮件。
他知道,有些问题不需要立即回答,有些归途也不是一张机票和一场出席就能完成的。
窗外,春风起。
那些曾被携往远方的文物,那些失落的文明碎片,终有一天会通过另一种方式回到它们该在的地方。
或许不是展柜,不是交易所,不是掌声,而是学者的手、工匠的刀、代码的算法,和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不曾熄灭的光。
他轻轻将信件存档,目光平静。选择权在他手里,也在未来。
注:1.本文前两章对话均为英文,考虑到可读性故没有用英文书写。
2.目前羊首下落不明,本文纯架空。
.jpg)
.jpg)